声援“五卅” 光华肇建
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国人民族意识日渐觉醒。爱国人士对西方教会学校开展的文化入侵痛恨不已,越来越多的进步师生投身收回教育权运动。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而诞生的光华大学就是历史见证。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籍师生听此消息激愤不已、积极声援。6月3日早上,爱国师生一致决定在校内升起国旗并降半旗志哀,然而学生的正义行动却遭到了美籍校方的强力压制。一位同学振臂高呼:“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圣约翰大学学生553人及全体中国籍教师17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这就是“六三事件”。
离校师生团结一心,迅速组织起来,决定“创立中国人自己的学校”,拥戴张寿镛先生创办大学,并定名为光华大学。6月3日也被定为建校纪念日。
创业维艰,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靠的是社会各界的团结与自强。

学生家长王省三捐出大西路(今延安西路)90余亩私地,许秋帆赠5000元,张寿镛先生除自身捐款3000元外另发售建筑公债,离校师生向社会发行建筑公债,赴南洋募捐……义旗高举,闻者景从。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纷纷资助,众多沪外的爱国学子也闻义而徙。包括武昌博文书院、安庆圣保罗中学以及扬州美汉中学在内的众多教会学校的离校学生纷纷前来报考。
在张寿镛校长精心筹划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诚支持下,9月12日,学校在霞飞路校舍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新校舍也于1926年9月落成。

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更要办“好大学”。光华大学一步一个脚印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这是一所拥有理想信念的大学。
光华大学的校名便出自“日月光华”一句,表达了复兴中华、反对列强的宏愿和光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光华人一直为“深沉纯挚的爱国观念”所激励,以启迪民众自强报国为己任。
这是一所兼容并包的大学。
强调民族独立,而非盲目排外。以张寿镛、朱经农、廖世承为代表的掌校者们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批判性汲取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奄有其长,而抉去其短”,努力做到新旧融合、中西贯通,为我所用。光华大学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在当时是具有先导性的。

这是一所强调知行合一的大学。
从“知行合一”到“格致诚正”,光华大学的校训始终贯彻“重学术、崇自由、务实际”的办学思想。光华大学的教育不仅注重理论教学,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便利,引导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实用型人才。
这是一所大师云集的大学。
一批学问渊博之士汇聚于此,成就事业。如吕思勉、何炳松、童伯章、吴梅、张歆海、徐志摩、李石岑、蒋维乔、胡适、潘光旦、廖世承、刘湛恩、郭任远、朱公谨、颜任光、胡刚复、杨荫溥、陈茹玄、张东荪、王造时、彭文应等。时人评价“上海各大学之师资,以光华为首”。
这是一所师生敬业乐群的大学。
学校全面落实“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特别注重“学生自治”。充分吸纳学生参与管理,以培养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据校友回忆“在简陋的饭厅里可以听到鲁迅、林语堂的演讲……在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张歆海和徐志摩在谈诗,李石岑在谈人生哲学。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奋发学习,蔚然成风。”这是光华大学成长时期的写照。
这是一所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光华师生成立抗日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筹募抗日经费,倡导宣传革命思想。在校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创办《文学丛报》,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而奔走呼吁。光华大学一度成为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光华大学的成功创办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光华大学所开创的兴学报国之路,垂范世人,为越来越多的后学钦慕和追随。光华大学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校风教风对学校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播迁火种 创建蓉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区在日军炮火下化为焦土。“战事当头,教育不能荒废”,光华大学校董会决议在四川设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并委托校董、商学院院长谢霖先生筹建。于是,光华大学教育报国的种子播迁到成都。

1938年3月1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在王家坝街租赁校舍开学。1939年,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新校建成启用。在谢霖副校长的精心操持下,光华大学上海本部的“老班底”薛迪靖、容启兆、李恩廉、周有光等再次组织起来,在成都续写着光华大学的办学传奇。
这部传奇也留下了许多川籍人士的名字。四川拨款五万元襄助学校,川绅张仲铭、富安、寿龄三兄弟捐赠杜甫草堂西郊五十余亩作为永久校址,四川自流井及贡井两场盐商热情赞助二万元建筑经费……1938年张寿镛来蓉参加首届毕业典礼,有感于川人的“好义敦厚”和蓉校办学的“相当成绩”,回到上海后复函谢霖“光华大学虽为避难分设入川,然亦正可藉此在川留一永久纪念以谢川人,既有上海光华大学造就东南学子,又有成都光华大学造就西南学子,将来扬子江上下游两部毕业同学合力报效国家社会,东西辉映,岂不懿欤?”

1939年1月,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迁入新校。此地也由此得名“光华村”并一直沿用至今。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在参观学校后予以高度评价:颇有相当规模,劫后得之,殊非易易。
成都分部一方面接收含光华大学上海本部在内的战区失学学生继续学业,另一方面主动支持抗战,为支援大后方造就实用人才。
良好的声誉吸引了大批战区失学学生涌入光华。面对经济困难、生活无法维持的学生,学校一视同仁,设法补助,使其能安心读书,甚至是携带年幼弟妹来校的,成都分部附属中学或附属小学也会为其提供读书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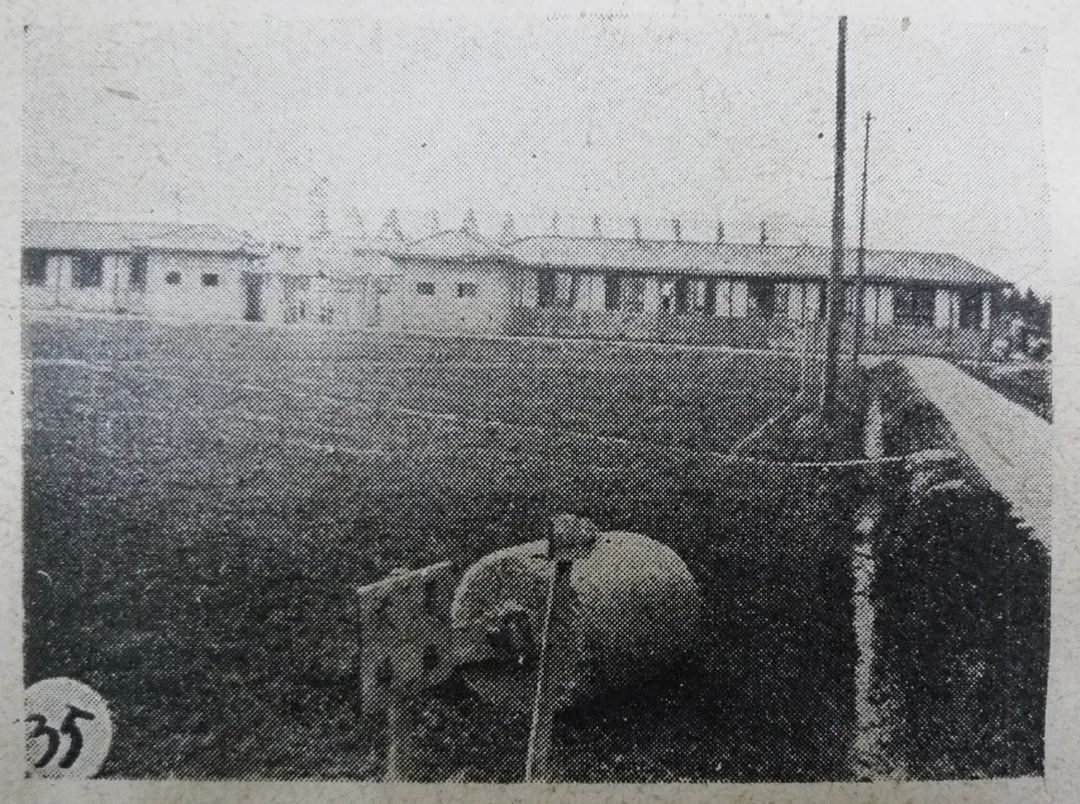
1938年,学校多次接受难童共200名,这些孩子以保育生身份入读光华大学附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谢霖副校长夫人张慧卿女士亲自担任保育生管理员,料理衣服、饮食、疾病治疗等事宜。学校经常以光华精神勉励他们,饮水思源、胸怀祖国。保育生也抱着坚定的爱国情怀走出光华村,有的考入军事学校,为抗日救国出力。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沿用光华大学文、理、商三个学院设置的同时,更加强调“经世致用”,突出商科特色,增设会计专修科,主动服务地方及战时需要。这一举措进一步增强了光华大学商科办学优势,也确立了以商科为主体的办学传统,为学校赢得了“学会计到光华”的社会声誉。
截至1945年,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大、中、小学三部共培养3164人,毕业学生2352人,其中大学生1563人,川籍约占80%以上。成都分部延续了光华大学的优良校风学风和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促进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和储备了大批社会急需的经管类专业实用型人才,谱写了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壮丽诗篇。
扎根西南 更名成华
1945年抗战胜利,光华大学决定在上海复校。鉴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校不得在异地永久设立分校”的决议,光华大学董事会致函教育部,拟遵照张寿镛校长和谢霖副校长当时商定的成都分部留川计划,将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转交川人接办。学校更名为成华大学,即成都光华大学之意,与上海光华大学成为兄弟学校。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复光华蓉校交办川人。1946年2月1日,成华大学正式成立。成华大学是内迁高校在抗战胜利后唯一一所上规模、整建制并留存四川继续办学的学校,“为迁川各大学仅存之硕果”。

成华大学许多院系都沿用了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设置,其中商学院增添了财政金融系、统计会计系等系科。原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学生中,大部分仍以借读生身份在成华大学继续学业,原管理人员、教师也大部分留在了成华大学。除续聘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知名教授外,成华大学还聘请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先后在此任教的知名学者有:萧公权、谢霖、潘大逵、薛迪靖、杨佑之、庞石帚、黄宪章、凌均吉、熊子骏、周太玄、李培甫、谢文炳、刘星垣、彭迪先、邓作楷、江子能、李炳英、杨声、李崇伸、归润章、吴家齐、左治生、温嗣芳。他们共同为传承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一脉和成华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成华地下党支部团结广大师生,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等学生进步团体,参与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爱国活动和护校斗争。
1949年12月底,成都和平解放,成华大学开启新生。
1950年,学校接受军管,在成都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开展全面改造,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学校组建教学研究组,改革实践教学,探索与新中国高等教育要求相适应的师资队伍建设。在原有会计专修科基础上,增设实用性强的企业管理专修科和统计专修科等,同时新设财经干部培训班,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一批急需的财经专业人才。

至1952年7月,学校培养本科毕业生共计2243人,加上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在成华大学的借读生,成华大学办学6年多时间,共培养学生3231人。他们很多人扎根川、渝、云、贵,迅速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光华大学创办之初就被赋予了追求教育独立自主、兴学图强、复兴中华的强烈愿景和历史使命,从光华大学到成都分部再到成华大学,学校从肇基上海到扎根成都,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形成了自立自强、兴学报国、格致诚正、复兴民族的光荣传统。光华大学成都一脉为新中国在西南布局一所社会主义财经大学积蓄了力量。